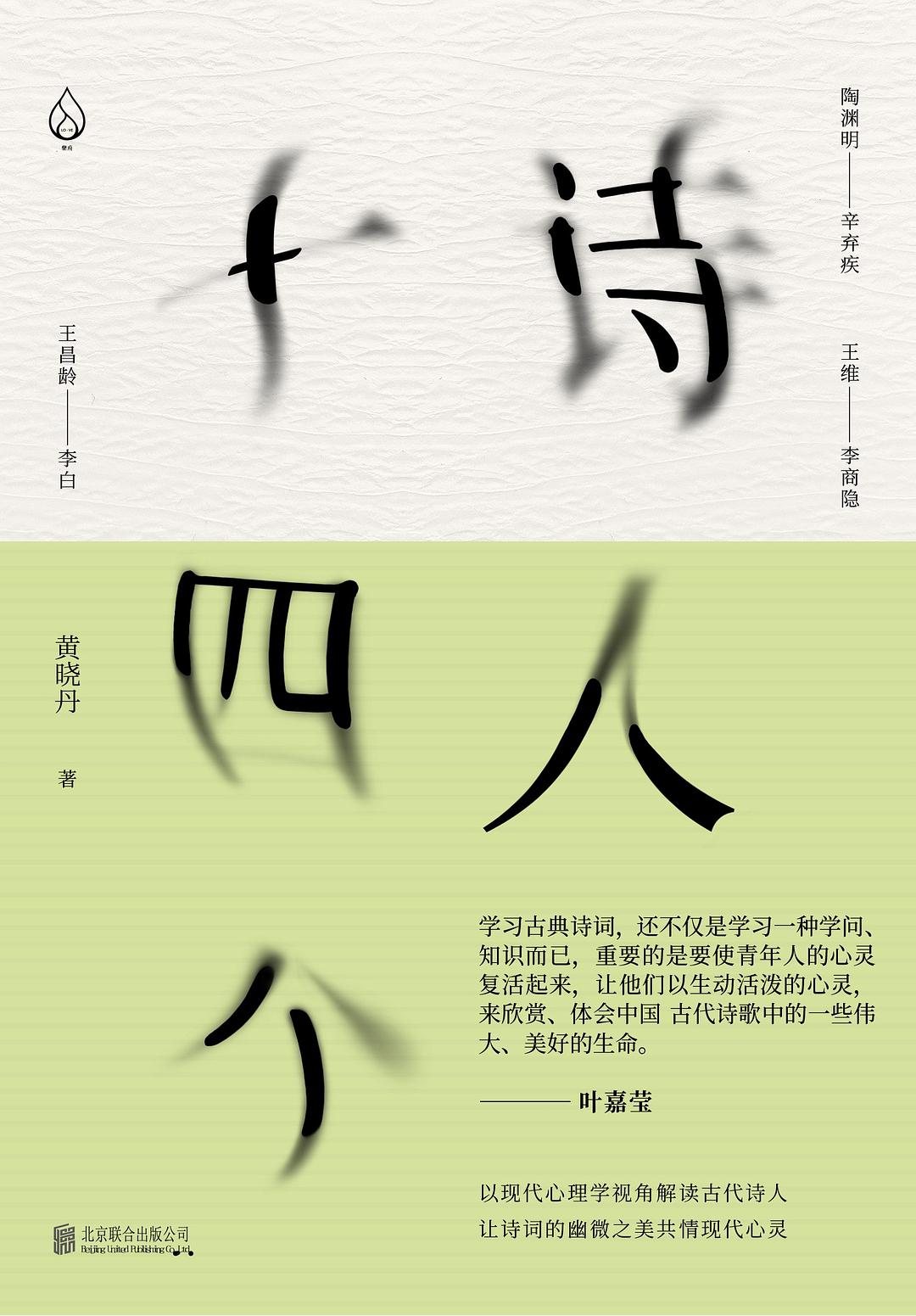高阳台
桥影流虹,湖光映雪,翠帘不卷春深。
一寸横波,断肠人在楼阴。
游丝不系羊车住,倩何人,传语青禽?
最难禁,倚遍雕阑,梦遍罗衾。
重来已是朝云散,怅明珠佩冷,紫玉烟沉。
前度桃花,依然开满江浔。
钟情怕到相思路,盼长堤,草尽红心。
动愁吟,碧落黄泉,两处难寻。
好一个桥影流虹,真美。
再看一眼,一眼就要老了
吴江叶元礼,少日过流虹桥,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,竟至病死。气方绝,适元礼复过其门,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,叶入哭,女目始瞑。友人为作传,余记以词。
紫玉烟沉
“紫玉烟沉”讲的是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。紫玉与一个叫韩重的普通人私定终身,韩重担心自己太平凡,无法被夫差接受,就约定学成归来再去提亲。三年后他学成归来时,才知道紫玉已经因为思念而死。当他到达紫玉坟前,紫玉的魂魄现形,二人抱头痛哭,同住三日并成夫妇之礼。之后,紫玉将一颗明珠交给韩重,让他持此信物告知夫差成婚之事。但夫差认为韩重是个盗墓贼,就把他抓了起来。于是紫玉跑到父母的宫殿现形,二老也非常思念女儿,上前抱她,可是刚刚一触碰到紫玉的形体,她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了。
春在堂前的花落了
我对俞樾不太了解,对他的印象来源于三件事。一是大学时在曲园游玩的经历。二是俞陛云的《诗境浅说》。俞陛云由祖父抚养长大,俞樾给俞陛云编的教材叫作《曲园课孙稿》。俞陛云长大中了探花,可惜不久后科举废除,接着清朝灭亡,他不愿出任伪职,就也在家编教材教孙子孙女学诗,《诗境浅说》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三是因为我关注清代的女性写作,所以对那些特别愿意教女儿读书写诗的父亲大有好感,而俞樾就是这样一个父亲。从俞樾到俞平伯,这个家族大致给我一种通达、乐观的感觉。
修养,家教
白首忘机
“白首忘机”用了《列子》里的一个典故。有一个小孩住在海边,和鸥鸟关系很好。他每天只要伸出手来,海鸥就会飞到他的手上,有时候全身都站满了鸟,他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。可是有一天,不知什么原因,可能有人告诉他这事不简单。他忽然意识到吸引海鸟原来是种不同寻常的能力,就想等海鸥下次落在自己身上时,带它们向别人炫耀一番。当他刚产生这种想法,就再也没有一只小鸟落在他身上了。《列子》把小男孩在瞬间产生的要让一只鸟飞到身上来的动机称为“机心”。在此之前,他对海鸟的飞落只是自然地接受,任其来去。而一旦想要把控这个确定性,和谐就会消失。
所谓赤子之心,本无一物。
飞升带来的是什么?用李商隐的说法,是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,是因为享有了极大的、没有边界的自由,而感到与真实的人类情感失去联系的孤寂。“存在”可以忍受孤独,而“意义”这种东西,必须建立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上,失去这种联系就会堕入虚无。人类心灵的诉求有一些原始的准则,我们希望同时享有“海上生明月”的超然和“天涯共此时”的亲密,艺术如果只是偏向对寥廓与清冷的诉求,将会变得无聊,如果只是偏向对人情人欲的呈现,就会变得琐屑。
空翠烟霏
一天,有个朋友来看我,我们围着湖走了一圈,后来他一直说“那天的湖真美”。但是我们无法向其他人描述那究竟是怎样的美。它的大小怎样,水质如何。朋友讲的不是这回事,他讲的是在春天美好的天气里和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相会,沉浸在一切都刚刚好的感觉里。 所以,这个男孩说“这个湖真美”和苏轼说“春山好处,空翠烟霏”是一回事。这样的“好”是不可被拆解的整体,是两个人各自的美妙与世界的美妙恰好在一个时间点上相遇。这种难能可贵的相遇足以抵抗历史带给我们的虚无感。
“空翠烟霏”是无法完全翻译的。从字面上看,只是说半山腰上有江南春天的湿气,有袅袅的云雾和深深浅浅通透的绿色。但这只是它的客观面,至于被主观赋予的美感,则要靠读者去自己的记忆中挖掘。这种美是秘密的契约。
现代人处理自己人生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,有时我觉得文学阅读也能起类似的作用。诗人用作品呈现自身的困境和绝望,同时也将他们抵御绝望的能力贯注在诗歌中。当我们在文学中穿行,体验这些非常尖锐的痛苦时,又无时无刻不被富有人情味的智者所牵引,所陪伴。等我们走出诗歌,过往生命中的伤痛好像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疗愈。
文字可以治愈。
春去的遗响:周邦彦与晏殊
有那么几个时刻,威廉·斯通纳意识到自己在使劲屏住呼吸。他把气息轻轻地舒吐出来,刹那间发觉自己的呼吸从肺里排放出来时,衣服随着身体在起伏。他把目光从斯隆身上移开,打量着教室。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,落在同学们的脸上,所以感觉光明好像是从他们自身散发出来,迎着一片黑暗释放出去;一个同学眨巴着眼睛,一道浅浅的暗影落在面颊的一侧,上面的毫毛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。斯通纳开始感觉放在桌上紧紧攥住的手指松开了。他在自己的凝视下掉转过手来,很惊奇它们都是黄褐色,很惊奇指甲已妥帖地嵌进粗壮的指端那种复杂的结构;他想,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血液在无形地穿过纤细的血管和动脉流淌着,从指尖到整个身体微弱又随意地颤动着。
我通过跑步也有过同样的感受。
浣溪沙
一向年光有限身,等闲离别易销魂。
酒筵歌席莫辞频。 满目山河空念远,
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
在珍珠里放一枝荆棘
我很难否定这样的看法,毕竟现代人认为健康的人格是稳定、开放、表里如一的,晏殊显然过于压抑。但我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,也许是因为自己正步入中年。当热烈的青春过去、旷达的迟暮还没有到来,清醒与自持,也许正是中年岁月最需要的给养。
叶嘉莹《唐五代名家词选讲》
悲剧的精神有两点特色,一是要奋斗挣扎的努力,二是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。
然而“真”在本质上也有不同,一种是刮垢磨光后像真金美玉般晶莹精粹的“真”,另一种则可能是未经琢磨的本质的“真”。无论敢以哪一种“真”与世人相见的诗人和词人都不多,只有陶渊明是“豪华落尽见真纯”。李后主也是“真”,但截然不能与陶渊明相比,陶渊明是最富思想性的诗人,他“一切景语,皆为情语”,而所有的情语又皆是思语。陶渊明的思致是非常富有反省和节制的,没有一点任纵的地方,他的感情是澄澈晶莹的。这一点可以说是古今诗人都难以企及的。至于李后主虽然也能以真纯与世人相见,但他却最缺少反省,缺少节制。
一般说来,我以为对人生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类型。一种是外延的,所谓外延者是指对人生的体验要与周围许多事物结合起来,即如王国维所谓“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”,他要观察的人生越广,才可以写出多方面的人生诸相。另外一种类型是内感的,是以真纯敏锐的内心本身去体验人生,不需要一件件事地去认识,这种心灵就如同一潭清水,如果他受到一块石头的打击,水面便会由这个打击点荡漾开去,达到一个博大的境界。这正是一颗纯真善感的心灵一旦受到打击,就会感到人间共有的莫大的悲苦的原因。